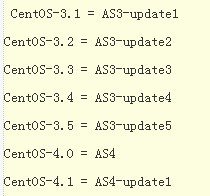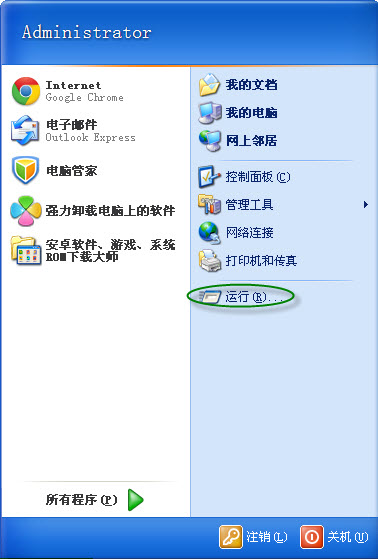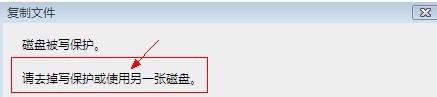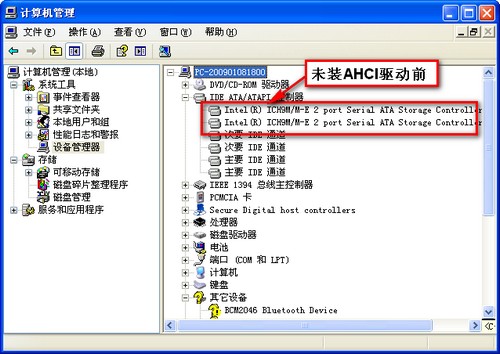【 小说节选 】
小说以复调的形式呈现海棠街的历史,勾勒出了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的众生群像,地理坐标之间的小人物衔接着历史与今天、人情和人心。
锈色海棠
万 胜
……
高月
高月的发廊开在海棠街上。海棠街旁边的小杨树林里有许多理发摊子,剪头两块,加五毛刮脸。一天下来对付个十块八块,晚上收摊,家什儿往自行车上一撂就走,头发茬子到处飞。高月的丈夫大安在沈阳学的美发,不想撂地摊,小两口就在海棠街边上租了间小屋,挂牌月安发廊。
大安剪头比地摊上贵很多,来的也都是敢花钱的潮人,捧得小店生意越来越火,只半年,高月就买下了出租房,又从里到外装修,上了个档次。平时高月负责给顾客洗头和收钱,一年后有了女儿琪琪,就把自己的弟弟从乡下找过来帮忙,又雇了外地姑娘小翠,自己只管带孩子收钱。等琪琪离手了,高月也跟着丈夫学理发。高月聪明,上手快。
房树德是发廊的常客,国营砂轮厂职工,办了停薪留职跑长途货运。他单身,为人豪爽,事看得明白,经常指点高月小两口,还老从外地给高月两口子带土特产。大安跟房树德特别投缘,就拜了把子。房树德比高月两口子大十多岁,尊称老哥。房树德不跑车的时候成天泡在发廊里,把配货的牌子摆到发廊的门口。发廊活少的时候,大安就让高月一个人应付,自己跟房树德跑车。房树德说,男人就得像孙猴子一样上得天入得地,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。大安尝了甜头就越来越不安分,没心思做理发生意,总在外面跑,当然也不白跑,偶尔会拿回来很多钱。这让高月的心有点不安稳,要是这么赚钱,那跑车的不都成了百万富翁了吗?有一天她这样问大安。大安给她打了个比方,说咱俩理发跟小树林里剃头的其实都一样,为啥咱就挣钱,他们就不挣钱?一指自己的脑袋说,就看这里,你放心,我就把握一条,有毒的不吃,犯法的不干。高月似懂非懂。自己的丈夫自己了解,算是个精明人。但她还是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,她发现大安和房树德的关系似乎出现了问题,大安自己跑起了单帮。
大安越跑越勤,最长的一次三个月没着家。房树德仍经常来,坐在那儿心事重重,还老直勾勾瞅高月,整个人陷入一种迷离中。高月有点不太自在,但也没多想。高月问房树德说,老哥,这些日子咋没见大安跟你在一起?房树德说,别提了,大安这小子,也就是我拿他当兄弟吧。高月觉得他话里有话,就说,老哥,我们两口子一直把你当成亲哥,弟弟弟妹有啥地方做得不对,你是骂是打都应该,就是不能看着不管,他不是做错啥事了吧?房树德说也没啥事,大安年轻,有点燥也正常。
两天后大安回来了,脸色很难看,对高月说这次买卖不顺手,赔了。高月说,赔就赔了吧,以后别乱跑了,有这个发廊也够活了。大安把头埋得深深的,许久不说话。高月说你有些事得多听听老哥的,他有经验。大安反问,这些天房树德还老来?高月心里纳闷儿,平时丈夫都是张口闭口叫老哥的,今天怎么直呼大名了呢?嘴上说,跟以前一样。大安只是哦了一声,没再说什么。
大安本分起来,整天带着女儿玩儿,和房树德的关系也恢复如初。高月的心渐渐安稳了下来。
这天,吃饭时房树德提到明天自己要去云南送货,而另有一批货在大连港需要拉回来,时间撞上了,他顾不过来,想让大安找一个托底的人帮忙跑一趟。大安说别找人了,我去吧。房树德说也行,那就让老弟受累了。第二天早上房树德把货车钥匙交给大安,嘱咐两句就走了。
大安跟高月商量,想把琪琪带着,琪琪已经六岁了,眼看就要上小学,还没看见过大海。高月没反对。看着琪琪乐颠颠被爸爸托上车,她突然有种莫名的心慌,有点后悔,转念一想,可能是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出远门的缘故,就按捺住了,笑着跟爷儿俩摆了摆手。
车走后,高月一直悬着心,老觉得忘了什么事,却又想不起来。吃过午饭,旁边食杂店的人来说老房打来电话找她。房树德在电话里问大安发车没,高月说已经走两个多小时了。顺便提了一嘴,说琪琪也跟着一起去了,大安要带她看看大海。房树德一听立即火了,说你怎么能让孩子一起去呢?高月被房树德的态度弄蒙了。房树德和她说话从来都和声细语的,这次怎么了?也许跑车有什么说道?赶紧说老哥,你别生气,就这一次,我保证。房树德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,缓了口气说,算了,不说这个了,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啊。房树德留了一个外地的电话号码,就匆匆挂断了。
高月心里越来越躁,还莫名其妙把小翠骂了一通。大半夜,食杂店的人来砸门,让她去接电话,仍是房树德。房树德说他刚接到交警的电话,大安在哈大道营口路段肇事了,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,让高月赶紧往营口交警大队去,他自己连夜往回赶。高月一下子蒙了。
高月到了才知道,昨天下午大安的车撞在桥栏上起火,大安当场死亡,琪琪重伤被送了医院。赶到医院时,琪琪还在抢救。大夫告诉高月,孩子属于特重度烧伤,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,而且双臂双小腿伤得太重,保不住了,必须截肢,现在情况很不乐观,希望家属做好心理准备。高月听着听着,一头栽倒在地。她醒过来时,看见房树德站在病床前。房树德告诉她,目前琪琪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,医药费他也都给交上了,不够他还会往里蓄。高月立即要爬起来去看女儿,房树德让她先坐起来缓一缓,然后搀扶着她去重症监护室。
隔着玻璃窗,高月看见被纱布裹得像小木乃伊的女儿,说这还是我的琪琪吗!身体支撑不住,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号啕起来。这是她从得到消息以来第一次号啕,之前都跟做梦一样,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高月和大安都没有老辈的亲人,大安的丧事是房树德帮着一手操办的。料理完后事,高月就把家搬到了医院,一门心思陪琪琪。发廊停业,小翠去了别的店。给琪琪看病需要很多钱,高月把发廊整体兑了出去,弟弟也另谋生路去了。这一场事故把高月折腾得家败人亡。她老是意识恍惚,好像这一切都不是真的,想让自己静下来,可脑子里有一架大飞机,忽悠一下子上天,忽悠一下子又落地,一刻不停轰隆作响。
琪琪清醒过来后一直喊疼,高月就成宿隔夜给女儿轻轻吹风,像喝热水怕烫,轻轻吹凉。其实她也知道这样做毫无意义,但她不忍心看着她疼,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开始几天她边吹边无声地哭,后来渐渐麻木了,吹着吹着就打瞌睡,头磕在铁床头上,磕醒了再接着吹。
房树德天天来,一待就大半天。他来了,高月就可以到走廊地上铺开垫子补觉,昏天黑地倒一会儿,睡着睡着忽悠一下子坐起来,六神无主地看周围,愣几秒钟起身就往病房跑。见琪琪躺在病床上喊疼,心里才踏实了。房树德用小纸扇轻轻给琪琪扇风,说高月,你也没睡多大一会儿啊,再去睡一会儿吧。高月说,睡不着。
房树德说,弟妹,你这么熬下去可不行啊,你要是把身子造坏了,孩子谁管?你为了孩子也得好好休息。说着把自己带来的水果递给高月。
高月接过水果放到床头柜上,说,琪琪什么也吃不了呢,她不吃我也不吃,等她能吃了,都给她留着。
房树德说,让你吃你就吃吧,等她能吃了我再给她买。
高月说,老哥,我家出这事儿多亏了你帮忙,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,你生意忙,别天天往这儿跑了,你帮我垫的钱,等我女儿好了之后我再慢慢还你吧,现在看病还不知道得花多少钱,我卖房子的钱也不敢动。
房树德说,什么欠不欠的,我没老婆没崽儿的,留钱没用,不用还了,不够我这还有。
那怎么行啊,高月说,大安出车祸的那辆车也得个十好几万呢,我们欠你的太多了。
房树德眼窝红了,说弟妹,你什么都别说了,我以后就把琪琪当成我的亲生女儿了。
高月也哽咽了。两个人面对面默然流了一会儿泪,房树德起身说,我先回去了,明天再来。
高月起来送到门口,说老哥,谢谢你了。
房树德走出门,没敢回头,出了门赶紧用手抹了把脸。
琪琪在半年中做了十五次手术,双手双脚都没了,浑身上下大面积植皮,又一时找不到匹配的皮源,就得先用猪皮代替。猪皮只是个过渡,等有了皮源还要重新做手术,剥下猪皮,植上人皮,折腾来折腾去的,遭了数不清的罪,一年就这么熬过去了。
植皮手术还算成功,没发生排异现象,琪琪一天天好了起来。住院一年多,高月手里的钱都折腾光了,只能出院,就想租间便宜的房子。房树德说你要是不嫌弃就住我家吧,反正我也经常跑车,你还可以帮我照看房子。高月想拒绝,但现实不允许,便带着琪琪去了房树德家。
房树德家在海棠街最南端的一片平房区,是国营砂轮厂的职工宿舍,虽然老旧,但房屋院落还是规规整整的。南屋大,高月带着琪琪住,北屋稍小,房树德一个人够用。
高月母女住进来的当天,房树德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子好菜。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香气,这让高月心里一阵阵感动。饭菜摆好,房树德放了四套碗筷,有一套是给大安的。又拿了一瓶白酒和三个杯子,先给大安满上一杯,然后给高月倒了半杯。高月说我不会喝酒。房树德说,得喝点儿。
高月说,我真不想喝。
房树德说,你听我说,这第一,琪琪死里逃生,多大的幸运啊,为了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得喝;第二,这一年多你在医院熬得够呛,今天咱们终于出院了,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,咱也得喝;这第三呢,你娘儿俩能到我家来,我心里是真高兴,这也是欢迎的酒,就更得喝。说完,他把自己的杯也满上,微笑着看高月。
高月端起杯轻轻抿了一小口,辛辣的酒抵住舌尖,把整个口腔都点着了,热辣的酒气呛得她呼吸困难,眼泪直流。房树德赶紧夹了口菜到她碗里说,赶紧吃口菜,压压。
琪琪已经能吃东西了,但需要高月一口一口喂。琪琪原来是个很活泼的孩子,现在整个人都变了,不说话,眼神空洞呆滞,烂纸浆一样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。唯一能察觉到她情绪变化的就是不知不觉从眼角滑落的泪水。高月喂她饭,她不嚼就往下咽,怕她噎着,高月得把食物做得又碎又烂。高月发现房树德做的饭菜也是又碎又烂的,而且她还发现整个房子里没有一面镜子,就连窗户也换上了麻玻璃。
高月被房树德的细心感动着,她无以为报,就尽全力收拾这个家,哪怕家里有一点点不整洁,她都会很自责。但仅凭这是不够的,她觉得这根本填补不了她对房树德的感激之情,她想让家里有一些新的变化,哪怕添置一盆花,换条新毛巾呢,但再小的东西也要钱买。可她没有钱,得想办法赚点钱啊。酝酿了好几天,她决定到区政府广场小树林里去摆摊剪头。这个比较简单,一把椅子,一把剪子,一把木梳,一个暖水瓶,一块围布,小喷壶,再加一面镜子就齐了。这天早上,高月准备好了一切,对琪琪说,女儿,妈要去小树林剪头了,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,等妈中午回来给你做饭,你想要什么,妈给你买回来啊。
琪琪没回应。
高月看着女儿的样子,犹豫了半天,一咬牙出了门。
高月在小树林里干等了一上午,没顾客,她刚要收摊回家给琪琪做饭,来了一个中年男人,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高月担心琪琪着急,就说大哥不好意思,我得收摊回家了。男人说,做买卖哪有你这样的啊,把顾客往外推,怕钱咬手是不?高月想了想,再看看男人的头发,也不是太长,用不了多长时间,便抖开围布,罩在男人的身上。
男人说,你觉着我这头发剪什么样的好看?
高月说,寸头吧,还好收拾。
男人说,也行。
高月刚要下剪子,男人又说,你下手可得有点儿数啊,下周我嫁闺女,别给我剪太愣。高月说,放心吧大哥。
剪着剪着,男人打起了呼噜。高月轻轻叫醒他说,大哥剪完了。
男人“哦”一声醒来,一照镜子,火了,你怎么给我剪的,这也太短了。
高月说,寸头嘛,都这样。
男人跳起来骂高月,你他妈的会不会剪头?我让你给我剪这么短了吗?谁家寸头这么短,这他妈的像臭鸡蛋长毛了似的,整这么砢碜你让我怎么见人……
高月明白,遇到无赖了,以前开发廊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人,只能认倒霉,就说,钱我不要了,你走吧。
男人说,你不要钱就完了,你把我的脑袋弄成这样怎么算?
高月不理他,闷头收拾东西。男人更来劲儿了,一脚踢翻椅子,你赔我形象损失费。
高月说,大哥,我从早上到现在就剪了你这一个头,没钱赔你。
男人说,不赔钱就别想走。
高月去拎暖水瓶,男人又一脚,把暖水瓶踢爆了。高月干脆什么都不要了,手里只攥着剪子,转身就走。男人追上来薅她胳膊,高月回身说,我活得已经很难了,你别欺负我了行不?
男人说,你少跟我装可怜,痛快点儿赔钱,今天不赔钱你走不了。
高月说,你还逼我是不?
男人说,你少他妈的跟我瞪眼,再瞪眼我削你信不?
高月突然发了疯,大叫一声,抬起右手朝男人的脸狠戳过去,男人抬手护脸,胳臂立即被剪刀戳出个血洞,男人飞起一脚把高月踹出五米远。高月窝在地上半天没缓过来。
经过民警调解,房树德给男人八百块了事。房树德搀扶高月走出派出所,说琪琪我都安顿好了,你别着急。高月脸色蜡白不停打嗝,说我腔子里有股气儿顶着,怎么也出不来。房树德说,咱慢慢走一走,顺顺就好了。
两人沿着海棠街向南慢慢走着。这条街是中心街道,最热闹,街上闲逛的人很多,懒懒散散的,走得也很慢。马路西侧是百货商店,东侧是东风浴池,再往前就是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。百货商场门前搭着一个台子,铺着红地毯。上面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,声嘶力竭地喊叫着。台子的一侧停着两辆崭新的轿车,另一侧摆着两大排新自行车。地上铺了厚厚一层废彩票。台子像是一个巨大的磁铁,把人吸过去。
房树德说,这事别往心里去,过几天我找人收拾收拾那王八蛋。
高月说算了,又给你添麻烦了。
房树德说,你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
高月说,我有点儿累了,歇一会儿吧。
两人在东风浴池的大门口停住,高月扶着路边的大杨树,大杨树有小脸盆那样粗,光滑的树皮上布满了眼睛一样的疤痕,这种疤痕是自然生长出来的。树身上掉了挺大一块皮,露着白瓤,虽然不至于要了树的命,但这块缺陷使杨树异常丑陋。高月轻轻用手抚摸着树的伤疤,哭了。
房树德说弟妹,咱还是走吧。
高月正要挪动脚步,忽然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从东风浴池里跑出来,站到大街上茫然四顾。那女人愣怔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没穿衣服,转身要往浴池里跑,就在这时,天地间突然爆出一声炸雷,大地震颤,整个东风浴池轰隆一下子从地面上消失了,一阵烟尘过后,那里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。高月站在深坑边上,魂都没了。
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地震了。高月不顾一切往房树德家跑,她知道女儿无法逃生。跑到房树德家,一切都平静了,琪琪安静地躺在炕上。高月说,女儿,别害怕,妈回来了啊。琪琪把脸扭向里侧,不吭声。高月给女儿掖被子,发现她的胳膊上有伤痕,用碘酒擦过,再看另一条胳膊上也有,回头看房树德。房树德用眼神示意她到外面说。两人走到院子里,房树德说,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琪琪在外屋地上趴着呢,是自己爬下来的,手臂和膝盖是在水泥地上蹭的,破了点皮,没事儿。
高月立即跑回屋,搂住琪琪哭着说,女儿,以后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
第二天,房树德拎回来一辆新轮椅,把琪琪抱到轮椅上,推出屋子,在院子里转圈。这是琪琪住进房树德家之后第一次出屋。阳光很好,风很柔和,院子里的月季花也很漂亮。那些花都是房树德这两天置办回来的,各式各样,摆满了墙头房根。房树德还在院子西南角栽了两棵葡萄秧,说等明年夏天葡萄长大,爬满了架,就可以在葡萄架底下吃葡萄乘凉了。
琪琪成天待在院子里,盯着月季花看。虽然她还是沉默不语,还是面无表情,但高月觉得她的心情肯定会有好的变化。高月这些天的心情也不错,不单是因为女儿,也因为自己有了营生。房树德把小门房改造成小理发店,设备工具都配齐了。她工作和照顾琪琪两不耽误,来理发店剪头的都是住在这里的职工和家属。
高月常常恍惚,做梦一样,生活好像又回到了以前。有时候忙不过来,下意识地喊,大安,帮我把染发水拿来。接过染发水时,发现不是大安,是房树德,心里突然一紧,就又难过了。这种伤心不单是对过往的怀想,还有对房树德的愧疚。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是房树德给的,她无以报答。欠着人情的滋味是不好过的,何况是这天大的人情。她不是没想过把自己交给他,但现在的自己跟从前的自己可不一样了,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带着残疾孩子的寡妇,这两年被生活煎熬得身子也不再那么健康漂亮了,把自己贴给人家,不是还债,是又多欠了一笔债。
送走最后一个烫头的,已是半夜。房树德帮着打扫,说我刚刚看了琪琪,睡着了。
高月嗯了一声,说,老哥,你也早点休息吧,我自己收拾就行。
房树德扫干净地面,直起身,很专注地看着高月的背影。其实高月也用余光看见了镜子里的房树德。她感觉到了他目光里的异样,那种目光像是带热度的暗波,推送过来,罩住她,让她感到窘迫、焦灼、不知所措。
弟妹,房树德像是下了很大决心,吐出来的字都在微微颤抖,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高月没敢回身,甚至没敢抬头,什么事?老哥。
我……我知道我要是说出来,你可能会不舒服,但是我……
老哥,我欠太多了,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,你……说什么我都会同意。高月觉得自己的脸要烧着了,心脏里有个打夯机在工作。
房树德走近两步,说前些天跑车到外地,看见一些事情,心里就一直想和你说,这话我憋了好久。
你说吧,老哥。高月心跳太快,都有点要承受不住了。
弟妹,那我就说了啊,我在外地看见一个跟琪琪一样的人,在街上用嘴叼着毛笔写字,我就想咱们琪琪长大了得有个活命的本事啊,我们照顾不了她一辈子。
高月极速跳动的心来了个急刹车,浑身的血流突然就慢下来,脸倒是更红了,因为惭愧和更加的感激。她回过身勇敢地看着房树德说,老哥,我听你的。
房树德说,人不逼不成器,琪琪可能得吃点苦。
高月说,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来吃苦的吗?
房树德说,那妥了,你也早点休息吧,累一天了。转身要走。高月不知道哪来的勇气,一下抱住了他,说,老哥,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,要不是还得照顾琪琪,我连命都可以给你。
房树德仰头,闭着眼说,弟妹,我今天半夜要跑车,马上就得走,我走了你把门插好啊。
房树德走了。
高月插好了院门,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。她知道房树德不可能在大半夜出车,他是在躲她。羞愧自卑失落伤感揉搓着她的心,她觉得月光是冰冷的,孤独的冰冷,这种冷蔓延到全身,把血液都冻凝了。
琪琪躺在月光里,睡得不平静,在喃喃自语。高月很认真地听,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女儿醒着的时候一句话不说,几乎成了哑巴。她看着月光里的女儿想,说吧,说吧,把心里话都说出来。
妈……疼!
高月差点儿哭出声来。
……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2022年第11期